春秋时期,我国《管子·水池》曾记载: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”。《周易·序卦第十》写道:“有天地,然后生万物焉。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,故受之以屯。屯者,盈也。屯者,万物之始也。”这里的“屯”可解读为低洼处灌满了水。因此,从中可以知道:自地球出现后,才有生命;而生命起源于低洼屯水的地方。这都说明生命起源于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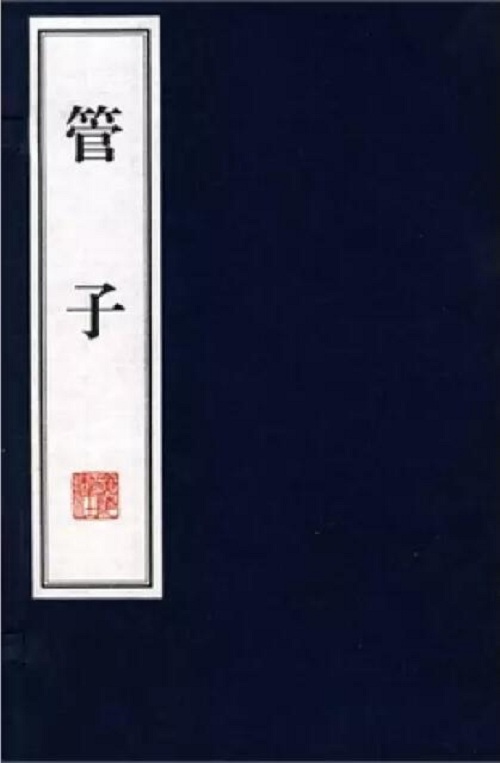
管子书影
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,“海,晦也。主乘秽浊水,黑如晦也”海这个字“从水从晦”。晦,便是晦暗。认为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,因此对海洋充满了敬畏和惧怕。而对于“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”的海边栖居的人来说,海洋又带给他们无限的恩泽,所以人类会举办祭海等仪式祈祷风平浪静,出海平安,鱼虾满仓,表达对海的感恩与敬畏之心。
面对着凶险的海洋,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探索的欲望,他们最先以丰富的想象来描写海洋的世界、山川道里、风土人情。比如著名的《山海经》,它里面的人物个个奇形怪状。“灌头国”其人“人面有翼,鸟喙”;“长臂国”其人“手下垂至地,捕鱼海中,两手各操一鱼”;“一臂国”其人“一臂一目一鼻孔”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:虽然山海经杂有一些传闻、神话,但它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,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。
先人也用神话来寄托征服海洋的雄心,比如精卫填海。它说的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女儿,叫女娃,趁炎帝出巡的时候,自己跑到东海向归墟游去,不料,一阵风浪袭来,把她吞没了。可是女娃的精魂没死,她恨海中的恶浪,于是化为一只鸟,“其状如乌,文首,白喙,赤足”,这就是精卫鸟,她发誓要填没东海。每天“衔西山之木石,以堙于东海”。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,于是精卫和海燕结成配偶,繁衍后代,让自己的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。

精卫填海
海洋的浩瀚使人类感到自身的渺小,苏轼曾感慨: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但海洋的奇幻神秘的魅力又吸引着人类去接近、去了解。当秋天的落叶在水面上随风飘荡的时候,人类从中得到启发造出了船。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独木舟的国家之一。到15世纪,中国的帆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、最牢固、适航性最优越的船舶。中国古代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,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。18世纪,欧洲出现了蒸汽船;19世纪初,欧洲又出现了铁船;到了19世纪中叶,船已经开始向大型化、现代化发展,而中国自明朝郑和下西洋后,开始海禁,对海上活动进行国家垄断,除非皇家许可,否则片板不能入海。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:在明朝,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,民众一出海便成为罪犯,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,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。而长久的闭关锁国,造成了海洋在中国近代史的缺位。海防武装仍是旧式水师,木质构造,从1840年起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。这也是为什么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结束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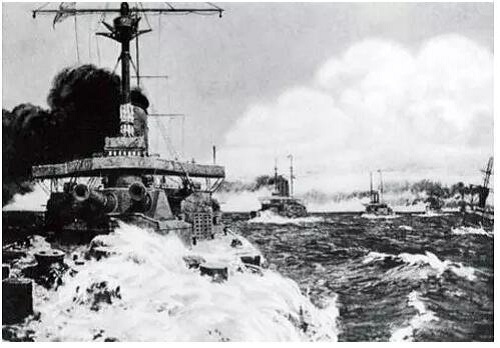
甲午战争
纵观海军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,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:一个沿海国家,长期漠视海权、轻视海防建设,必然会付出沉重代价,这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的历史结论。联想现今的中国南海仲裁之事,中国在南海军事演示展现的强大的军事实力,宣誓中国主权,寸土不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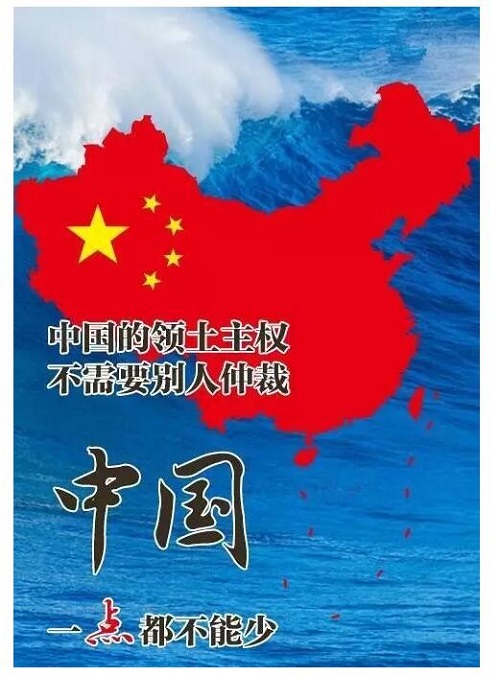
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,海洋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。面对严峻的海上形势,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发展,就要武装好自己的海洋测量装备,为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打下坚实基础,以应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。
中国,一点都不能少;中国的海洋探测装备,更加不能缺席!

中海达海洋产品

 中文
中文


















